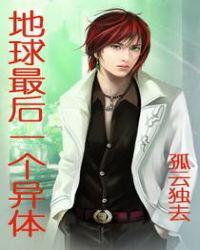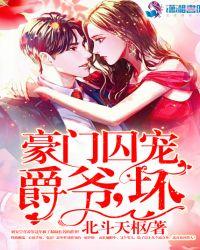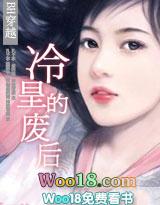落伍文学>女主对她情根深种[快穿] > 130140(第30页)
130140(第30页)
“可是最近也没人上吊啊,中元节那几天大家都安安分分的,只有钱老爷家的大少爷死了,刚好那天出殡,也没别的稀奇事了。”
一人用胳膊肘顶了顶说话的人,挤眉弄眼道:“怎么没有,你忘了,东街周姑娘就是他娘子。”
“你说周姑娘,哎,周姑娘也是痴情,竟然……”
提及死者,老百姓们都遵循死者为大,都摇摇头不再继续说了。
而且现在这环境,也不吉利。
“姑娘,你要的馄饨好了。”一碗新鲜热腾腾的馄饨放在桌上,叫回了陶宁出走的思绪。
那身形微胖的大娘用手擦擦围裙,看了陶宁一眼,咦了一声:“这位姑娘很面生啊,最近才来的广安县吗?”
陶宁不欲暴露身份:“我来这边投奔亲戚,昨天才到的。”
大娘应了一声,她看起来对面生的来客非常有兴趣,恨不得马上坐下把人寻根问底,奈何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正忙着呢。
正想着,就又有新客落座,要了一碗清汤面。
她只来得及匆匆说一句:“我这刘记在广安县开了几十年了,汤底用新鲜大骨熬出来的,姑娘好好吃,不够再找大娘添。”
陶宁:“怪不得那么香,我就是被这香味吸引过来的。”
语罢,她似有所觉地向一侧看去,一月白衣裙的年轻女子后半拍地收回目光,伸出两根细长手指:“要两碗。”
在灶前忙活的青年说:“还是和以前一样,一份要葱,一份不要是吧。”
年轻女子点点头,将手中食盒递过去:“钱我放在这了。”
刘娘子一边下面,一边说:“好多天都没见着静娘你了,身体可好了些?”
被唤做静娘的女子弯起微白的唇,她身形纤弱,像是一朵风就能吹走的白梨花,轻声细语道:“我好多了,病重想念大娘家的手艺,现在好了就来买了。”
刘娘子笑得双眼微眯,手上干脆利落地捞起煮熟的面,窝进手上碗里:“你要是想吃早说啊,说一声我就送你家去,难为你那么多天不出门,还吃不上馄饨。”
那青年也道:“就是啊,戚姑娘你要是想吃了就让戚木匠说一声,我娘会给你送上门去,都是乡里乡亲的,不用那么客气。”
戚静:“好呀,下次一定会的。”
说着,两碗馄饨也好了,戚静提着食盒转身往家里走,看方向是东街。
东街那一片住着不少人,西街这一片则是集市,北街是昨天进门的主大街,那边则全是药材铺。
陶宁慢悠悠地把碗里的馄饨吃完,刘娘子可算逮到机会往陶宁桌前一坐,正准备说话,就见两衙役往这边快步走来,她只好又站了起来。
刘娘子:“两位要吃什么,馄饨没有了,面还有。”
衙役摆手道:“今天不吃了,少卿大人原来你在这,县令大人正四处找您。”
前一句话是跟刘娘子说的,后一句则是神色恭敬地对坐在一边的年轻女子说的。
埋头喝汤的陶宁:“……”
刘娘子及青年看看他们,又看看陶宁:“少、少卿大人?”
平头百姓的,见过最大的官就是本县县令了,从没听过什么少卿大人,但看两位衙役诚惶诚恐的模样,应当是官位不小了,也跟着诚惶诚恐起来。
已经到了午膳的时候,赵县令在县衙里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人回来,听说少卿大人在外头吃馄饨,生怕是自己招待不周,派人出来寻。
陶宁只好放下碗,对目瞪口呆的刘娘子笑了笑,侧过头就收起笑意,对那两衙役道:“赵融最好是有正事找我。”
“……”
两衙役一人望天,一人看地,不敢应答,用行动表示不是他们有意的,只是听命办事。
陶宁放下银钱,转身离开,中途经过李霁说过的巷子,驻足看了一会。
衙役看陶宁不动,他们也站在原地不动了,就见她往那边张望片刻,忽然举步往巷子深处走去。
今早上李霁说昨晚上她追着红衣鬼影,一直到了巷子尽头,然后那红衣鬼影就消失不见了。
她还说巷子的尽头是一口井,井上悬着轱辘,周边长满了杂草,早就被人放弃使用了。
衙役忙追了上去:“少卿大人去哪做什么,这口井死过人,阴气森森的,不吉利。前年有个汉子喝醉了掉了下去,脖子都摔断了,大冬天的整个人都冻硬了,真是造孽。”
陶宁步履不停,听这话不像是意外,便说:“死过人?凶手捉到了吗?”
其中一个衙役答道:“捉到了,那人因为欠了人家银子还不上,故意跟踪他把他推下井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