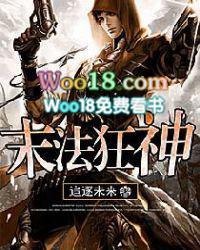落伍文学>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四十六章 想想余惟是怎么做的(第2页)
第二百四十六章 想想余惟是怎么做的(第2页)
可现在,这卷磁带告诉她:她写过。而且唱过。只是当时无人听见。
“是你自己埋下的。”马库斯低声说,“但不是‘你’??是十二年前那个你,把声音交给了这片土地。而现在,它还回来了,带着修改稿。”
林知遥瘫坐在椅子里,泪水无声滑落。
原来母亲从未真正离开。她以声音为线,织了一张跨越生死的网。而她自己,也在无意识中成为了这张网的一部分。那些她以为遗忘的痛、未完成的歌、说不出口的告别,全都被大地收下,封存,酝酿,直到今天才重新吐纳。
当晚,她独自一人爬上望月坡,把《回声Ⅱ》的磁带埋在巨石之下。没有仪式,没有言语,只是轻轻覆土,然后盘膝坐下,任山风穿过发间。
月亮升到中天时,她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是孩子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王小花抱着她画的《大地在学说话》,李同学拎着一台改装过的便携拾音器,放牛娃捧着一截从老槐树上自然脱落的枯枝,马库斯则背着那只装满笔记的木箱。
他们一句话没说,围着她坐下,面向月亮。
许久,王小花轻声问:“老师,我们以后还能听见更多吗?”
林知遥望着天边渐隐的星辰,缓缓道:“只要我们不停止倾听,声音就会一直生长。它不会停止,因为它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李同学低头摆弄拾音器,突然抬起头:“我在想……如果声音能记住我们,那我们能不能也记住它?不是用录音,不是用文字,而是用身体?”
林知遥笑了:“你已经在做了。你每次分析波形时的眼神,放牛娃哼歌时的呼吸节奏,王小花画画时的笔触??这些都是在‘记住’。”
马库斯忽然开口:“我在苏黎世实验室时,曾试图用AI模拟自然界的声音演化。失败了。因为算法无法理解‘意义’。但现在我懂了,声音的意义不在频率里,而在关系里。是你听它,它也听你的时候,才真正诞生。”
话音落下,山谷静得能听见雪融水渗入泥土的微响。
第二天,林知遥宣布要办第二场实验:**声音移植计划**。
“我们要把山里的声音,种到城市去。”她说,“不是播放录音,而是让城市‘学会’这些声音。”
计划分三步:第一,选取五种最具“生命力”的山野之声??钟楼自震、井底嗡鸣、槐树心跳、溪流共振、以及雷雨夜铜钟的三十七响;第二,将它们转化为可植入式音频模块,嵌入特制陶片;第三,把这些陶片秘密安放在城市五个角落:地铁隧道壁、废弃电话亭、公园长椅下、图书馆书架夹层、以及一座老教堂的彩窗缝隙。
“我们不告诉任何人。”林知遥说,“就像母亲当年把《启寂》藏进病房录音一样。让声音自己寻找听众。”
行动在深夜进行。林知遥带队,马库斯负责技术封装,孩子们每人守护一块陶片。他们在京城游走,像一群现代巫师,默默埋下声音的种子。
一个月后,异象开始出现。
一位地铁检修工报告,凌晨三点,隧道墙壁会传出类似钟鸣的低频震动,持续七分钟,随后消失。声学专家检测无果,称“可能是结构疲劳”。
一名流浪汉常在废弃电话亭过夜,某天突然对警察说:“里面有女人唱歌,调子怪,但好听。”警方搜查未发现设备,驱逐了他。
图书馆管理员发现,每当有人在特定书架前停留超过十分钟,耳边就会响起极轻的水流声。起初以为是耳鸣,后来多人反映相同现象。
最离奇的是教堂。神父在弥撒中突然中断祷告,泪流满面:“我听见了童年时溪水的声音……我以为我忘了。”
网络开始流传“都市灵声”传闻。有人建立论坛,收集“听到奇怪声音”的经历。帖子越积越多,有人称之为“城市耳语”,有人怀疑是新型精神控制实验。
林知遥默默关注着这些消息,但从不回应。
直到某天,一个ID叫“听风者2049”的用户发帖:
>“昨晚我在图书馆,站在哲学区第三排,突然听见一阵树叶摩擦的沙沙声。
>那声音持续了九分钟。
>我闭眼,闻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气息。
>我三十年没回过乡下了。
>可那一刻,我想起了外婆家的院子,想起了蝉鸣,想起了她摇扇子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