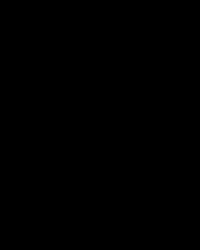落伍文学>我是限制文的女配 > 第29章(第5页)
第29章(第5页)
谢清鹤仍回答不出来,他被谢家庇护得很好,世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离他太远了。从小到大,围绕着他的都是好意。
见他答不上来,今安在说:“因为有情的帝王活不下来,他们有情,遇事就会优柔寡断,这对一个帝王不是什么好事。”
就像他的父皇一样。
短暂的寂静过后,谢清鹤忽问:“你明知京城对你来说很危险,为何至今还留在京城?”
今安在眸色渐凝,握紧长剑:“我要杀一个人。”
一年前,他试着去杀对方,但失手了,还受重伤,躲在乱葬岗里差点死了,这才被林听救下。
谢清鹤第一次听他提起此事:“你要杀谁?”以今安在的身手,只要不杀当今皇帝,杀其他人绰绰有余,怎么会还没成功。
今安在眼神充满寒意,冷漠道:“当今太子。我要他死。”
谢清鹤猛地抬眼看他:“太子身边有暗卫随行,个个武功高强,你怎么可能杀得了太子,这不是送命?”不想举兵谋反,却要杀太子,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他不为所动:“哪怕是送命,我也要与他同归于尽。”
谢清鹤不明白:“你这是要报灭国之仇?可你如果要报灭国之仇,该杀的不是当今陛下?”
“不是报灭国之仇,大夏本就气数已尽,到山穷水尽那一步了。不是大燕的皇帝,也会有旁人来取代大夏。我之所以要杀太子,是因为他欠我一条人命。”
说罢,今安在走上二楼。
一阵风从窗外吹进,吹灭了书斋里的蜡烛,周围陷入黑暗。
段翎却借着寥寥无几的月光仔细看暴露在空气中的另外两块软糕,它上面缀着一抹红,似是一粒红糖,而四周白皙,毫无瑕疵。
他的手覆上去时,软糕会微微陷下去,触感温热、柔软,散发着甜香,吸引着人去吃它。
段翎张嘴吃了。
没人吃林听拿着的那块绿豆糕,它最终掉回到碟子上。
待段翎吃完软糕,他们在案几前站了好一会才回到床榻。她这时候困得不行了,再加上站太久,也累得不行,想倒床就睡。
而段翎没给林听这个机会,将她捞了起来,接上断开的吻。
这一晚,林听睡得前所未有的安分,都不带翻身的,她还没帮段翎治好病,段翎就帮她治好“睡觉时会动手打人”的病了。
林听睡着后,段翎彻夜未眠,他躺在她身边,侧躺着看她。
她对此一无所知。
段翎看了半晌,下床榻走到镜子前。镜中倒映出一张美人脸,皮肤有未散尽的潮红,他新换上的绯色里衣微敞着,露出两截锁骨,往上点的脖颈戴着一条红绳。
红绳挂着个金财神吊坠。
那是林听迷迷糊糊时才勉强答应给他戴一晚的金财神吊坠。
段翎忽然发现自己连一个金财神吊坠都比不过,他一把扯下红绳,想将它往地上砸,却又硬生生地忍住了,又系回脖颈上。
段翎看着她朝他走来,转头对梁王道:“恕卑职难以……”
他没能把这句话说完,林听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爽快地喝下一整杯酒,踮脚亲了上来,没给人任何准备,就连梁王也愣住了。
梁王没想到这舞姬性子这么野,寻常人不该先向他们行礼?
她倒好,赶着投胎一样。
林听连个眼神都没给梁王,左手利落捂住了段翎双眼,右手揭开紫色面纱一角,只露出抹了胭脂的唇瓣和线条优越的下巴。
看在外人眼里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喂酒情趣。
实际上是她不想露脸。
段翎也没料到她一上来就亲,不容拒绝似的。等他反应过来,林听口中的酒已经顺着唇角进入了他唇齿间,染着熟悉的女儿香。
两唇厮磨着,混着酒水。
段翎要往后退,推开她,眼神古怪。可才刚分开一点,林听迅速用手按住他后颈,又亲了回去,溢出来的酒水沿着她唇角滴落,有几滴砸在他手背上,发着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