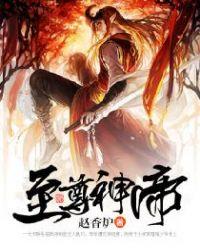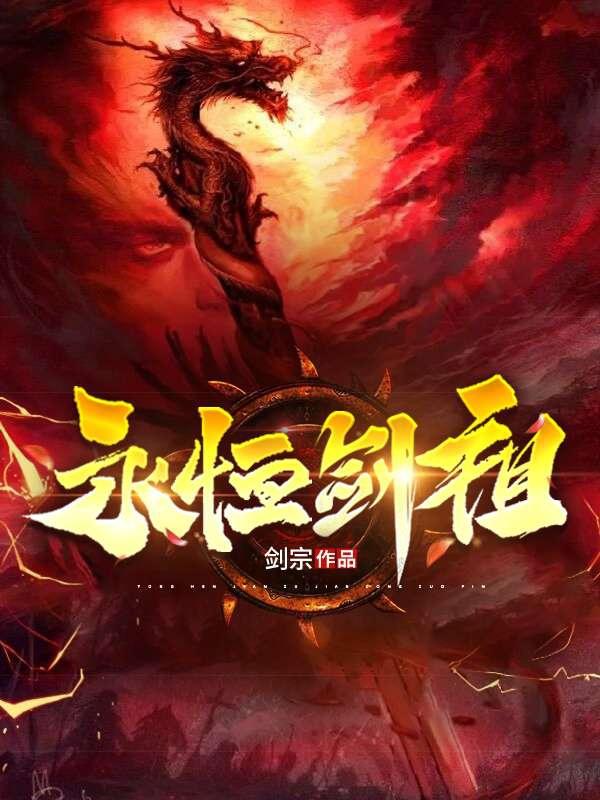落伍文学>位面小蝴蝶 > 第108章 向北(第1页)
第108章 向北(第1页)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省份,这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原。
在中国任何一政权占据了河南方才有资格称得上是正统。
河南的人口众多早在战前这里拥有九百万人,这几年的战争下来人口有所下降,人口依然在六百万以上。
战乱对这个富庶的地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自耕农完全消失,存在下来的都是结寨自保的大地主势力,这些势力在过去一直在红巾军和元军两边摇摆,在红巾军大势已去的时候纷纷落井下石。
当然现在河南已经是这些势力的地盘,原先河南的元朝的元军早已被消灭,现在的元军实际上是元朝迫不得已出现的民军,其性质和晚清时曾国藩的湘军是一样的。
其上层为了儒家宣扬的君臣大义而战,在这里必须说的是那些儒生已经将孔子的华夷之辨玩坏了。
红巾军的以战养战的发展对这些地主利益有着损害,所以这些地主们就开始宣扬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元朝皇帝为华夏之君,按照君臣大义,为天子平定天下。
反正这些人在北中国垄断文字,孔子的那几句话他想怎么调教就怎么调教,这跟后世媒体随意剪辑视频采访是同一种手段。
红巾军破坏了北方中国当政者拉拢地方大户的潜规则,红巾军由农民崛起,这些农民一旦翻身,对这些过去看来高高在上,现在面对自己大军无比柔弱的地主老财们没有清醒的认识,红巾军没有了解整个华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具有多大的力量。
在战争后期,这些地主出人出钱,为元军剿灭北方红巾军出了大力。
现在河南的形式立刻不一样了,河南的土豪们面对的是一支比红巾军厉害百倍的群体,首先这支军队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有着自己的思想,在程攀所谓正统大道,人人生来平等,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思想武装下,河南地主们那些玩弄圣人遗言的文字游戏没有任何说服力。
而且自己都没有信心反驳共合的理论。
最大的体现就是严禁共合的书籍扩散,同时时刻关注着佃户们的动向。
思想上的威胁还是轻的。
河南畏惧共合的最大原因是,共合无需地方绅缙的配合,就能管理半个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河南士林知道这是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宗族势力是无用的,红巾军在北方闹来闹去,最根本的却无法解决治下民众的吃饭问题只能靠以战养战拖着,一旦遭受失败就会立刻一蹶不振。
但是共合不同,共合的治下民众各行其职。
工厂中出产钢铁,大片农田中长满粮食,共合有能力解决河南大众的吃饭问题,能组织河南人生产。
世界与你为敌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用,世界有你和没你一个样。
主持攻击河南的主帅何成是第一次指挥这么大兵团作战,和会战不同,会战是两只主力部队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开打,以消灭对方的主力部队为胜利条件。
但是大兵团进攻不同。
何成手下十六个师中的十个,以一条战线的形式向河南压过去,何成在战线后头布置的军队随时充当预备力量对一线部队实行支援。
何成为了掌握一百多公里战线的动向,最头疼的是消息传播问题,马匹信鸽各种信息传递媒介都用上了。
何成的战线推进的比较慢,但是十分稳,稳的对面无语。
共合的大军像一阵山一样压过来,火力不够的元军没法对着这个一字长蛇阵般的军阵实行任何一点的突破。
原本适应和红巾军一起火器为辅肉搏为主的打法,在面对共合军死亡之雨般的炮击,以及狂风般的子弹,没有一支力量可以坚持,在共合的优势火力下河南元军放弃了聚集力量寻求在共合一点打击。
将人送在共合炮口下的简直就是送炮灰。
至于河南宝贵的骑兵和鹰炮组合的军队,骑炮结合的战术是需要找到对面的薄弱点实行突破,至于现在对面上百公里处没有薄弱点,鹰炮的射程没有共合军的火炮远,骑兵更是宝贵,元军将领舍不得将他们的心头肉投入这个有去无回的绞肉机中。
也就是在共合军的稳扎稳打下,孛罗贴木儿向朝廷发出了“共合军势大,河南局面不可为”的战报。
朝廷中的七王爷很有魄力,他下令让河南元军保存实力,带走足够的物质和工匠向北退。
河南元军的北逃让河南的大户倒霉了,孛罗贴木儿抱着临走捞一票的思想,加上前线的民军对共合军没有抵抗力而且损失很大,元军统帅是蒙古人手下的骑炮部队也都是蒙古人,既然要走了就对帮助元朝剿灭红巾军立下大功的当地大户见财起意,首先把从当地招的民军调到前线,然后就对这些养了几年的肥猪们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