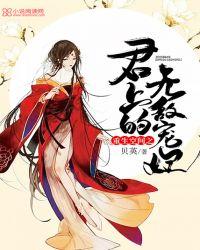落伍文学>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四十章 盒中盒(第3页)
第二百四十章 盒中盒(第3页)
>“今日方知,天赋不在技巧,而在感知。李姓少年虽未受正规训练,然其耳聪胜于多数学院出身者。他能辨水流之律,识风过之形,此乃‘生声’之根。或可言:真正的音乐教育,不应始于乐理,而应始于失语??让人先忘记规则,才能重新听见世界本来的节奏。”
夜深后,她独自登上村外最高的望月坡。山顶立着一块风化严重的界碑,刻着模糊不清的地名。她掏出竹笛,却没有立刻吹奏,而是先坐了五分钟,如她要求学生做的那样。
她听见:
南坡松林簌簌,似有猫头鹰振翅;
北岭传来牧羊犬吠,三短一长;
西面山谷,某户人家还在舂米,节奏稳定如心跳;
东边,则是远处国道偶尔驶过的货车轰鸣,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回声。
然后,她缓缓举起笛子,吹出一段全新的旋律。
这不是任何已知曲调,也没有明确结构。开头缓慢低沉,如同夜行者的脚步;中间转入一段跳跃的节奏,仿佛孩童追逐萤火虫;最后则是一串悠长的滑音,像目光投向无尽星空。
她一边吹,一边感受指尖与木笛的温度交融。这支笛子早已不只是乐器,它是母亲遗物的延续,是旅途的见证,是无数个夜晚孤独思索的共鸣体。
当最后一个音消散在风中,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不是成功,不是成就,而是一种归属感??她终于不再是谁的女儿,不是“静默协议”的象征人物,也不是某个传奇作品的创作者。她只是一个会吹笛子的人,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个角落,用声音回应着世界的呼吸。
第二天清晨,村里来了几位陌生人。
他们背着摄像机和录音设备,穿着朴素但专业感十足。带队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找到村委会打听:“请问林知遥老师住哪儿?我们是‘素声计划’纪录片团队,想拍摄一期关于基层声音教育的专题。”
村干部正要回答,却被一个身影抢先。
“她今天不上课。”李同学挡在门口,手里紧紧抱着笛子,“老师说,上午要陪我去采菌子。”
摄制组愣住。
男孩挺直腰板:“你们要是真想拍,就等我们回来。但不能打扰她练功,也不能让她讲那些大道理。你们要是只想拍个名人故事,那就请回吧。”
镜头后的导演沉默片刻,摘下耳机,轻声对同伴说:“把设备收起来。我们等等。”
三个小时后,林知遥和少年满载而归,篮子里装着新鲜的松茸和牛肝菌。她看见摄制组仍站在原地,不禁一笑:“你们还没走?”
“我们想拍真实的你。”女导演诚恳地说,“不是作为‘林知’,而是作为一个正在做这件事的人。”
林知遥看了看身边的少年,又看了看那些收起的机器,点了点头:“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所有素材未经我同意不得公开使用;第二,你们必须参与一次‘沉默训练’??跟我一起坐满三十分钟,什么都不做,只听。”
对方毫不犹豫答应。
当天下午,五人并肩坐在晒谷场上。烈日当空,蝉鸣刺耳。起初,摄影师频频看表,录音师下意识调整麦克风角度。直到林知遥轻声说:“放下设备,闭上眼睛。”
二十分钟后,有人眼角湿润;二十五分钟时,一只蝴蝶落在导演肩头;第三十分钟结束,全场寂静。
没有人说话,但彼此的眼神已不同。
几天后,摄制组悄然离去。他们最终只拍了不到十分钟画面,却在后期剪辑中反复播放那段无声的沉默片段,配上字幕:
>“这里曾什么都没发生。
>但也发生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