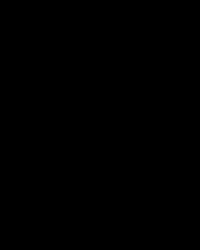落伍文学>暖栀[先婚后爱]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沈宴轻拍她的肩:“别怕,放轻松。我们不算完全陌生,你已经有些熟悉我的节奏了,不是吗?”
他口中的熟悉,是先前两人隔着衣服做过类似的事。
宋暖栀忽然明白过来,沈宴婚礼之前让她一步步熟悉他,就是为了此刻。
一如他商场上的运筹帷幄,在男女之事上,他也像一个精明的狩猎者,一步步给她下诱饵,再引她落进陷阱,成为他盘中之物。
适应了黑暗,借着袅淡的月色,宋暖栀依稀能看到男人英隽利落的脸廓。
她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
沈宴依旧向先前在客厅时那样,从额头的位置一路吻上她的唇,又顺着纤细的天鹅颈向下。
裹着的浴巾被丢开,他在最温柔之地流连,在她贫瘠的土地上烙下朵朵红花。
宋暖栀五指探进他的短发里,隐忍咬住下唇。
好在他没多久又离开了,继续去下一站。
空调的凉风漫进室内,轻薄的纱帘细微浮动。
淡雅怡人的栀子花在月色下含苞待放。
沈宴仿佛置身花丛,所过之处,鼻端全是清新好闻的栀子花香。
可惜手上的这朵栀子花还很生涩,像是温室里娇养出来的,天然害怕外来的入侵,层层花瓣都紧紧收缩,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容纳。
他试着去亲吻安抚,很快,尝到满口花蜜。
被浇灌的鲜花总是绽放得格外绮丽,以惊人的速度在月色下盛开。
引来莺声婉转,酣畅淋漓。
……
宋暖栀大学期间最害怕的就是女子八百米体侧。
她没想到,新婚之夜还能拥有一次类似的体验。
其实这二者并不完全一样。
毕竟她还不至于在女子八百米体侧时把自己折腾哭,今晚却哭了好一阵。
沈宴先前的温柔绅士,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的哭泣求饶,换来的是更猛烈的摧残。
后来宋暖栀学精了,咬着下唇不哭出声,以为这样能够换来他的怜惜。
结果他更卖力,问她怎么没声了。
想着刚才种种,宋暖栀背对着他不想理人。
他太坏了。
两人的身上都出了黏腻的细汗,沈宴从后面抱着她,彼此的身体紧密相连,负距离。
他存在感强烈,宋暖栀小声催促:“你还不出来?”
他依依不舍般退开,传来细微的一声“啵”,宋暖栀被这声音羞得直接用被子蒙住脸。
沈宴轻吻她清甜的发丝:“我抱你去洗澡?”
宋暖栀的睫毛还是湿漉漉的,闻声急忙拒绝:“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