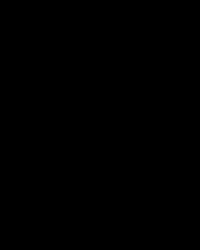落伍文学>陋篇(古言,NP) > 豫靖侯H(第2页)
豫靖侯H(第2页)
“公主不要这样夸我。”
文鸢闭嘴了,车行大道时,偷偷看他。
似乎以前与他说话,不怎么困难,无论说什么,他都要黏过来,文鸢文鸢的。不过是五年前的他了。宗室子身上常有的、无形的线,牵引他行动,他舔她的金链,强占她,同时把她当作热情的源头,十分依恋。现在又如何呢,文鸢嘴唇的血痣都淡去……
两人对视了有一会。文鸢回神,去看过楚鸟。
车行叁天,才到治城。文鸢见了曾掳掠她的县子弟,仍然心悸。子弟们懂事,不围着她转,帮豫靖侯换车去了。
长公主乘过的赤罽车,被豫靖侯当作家产,从西平道带往新的土地,这次正好有用。他让人照样做:“大一点。”一做耽误好几天。
“离齐国不远,不用做新车,乘原来的去吧。”
吃饭时,两人隔几。
豫靖侯装听不清:“乘原来的挤。”就这样留下文鸢,造车期间,给她宫池,给她帛画,还给她牵来一头鹿。文鸢半夜被舔,以为是鹿,好言劝说:“你在人居生活,本来有损身体,再不早睡,就完了。”“鹿”却过分亲热,碰她的鼻尖,吮她的下唇。
早起,文鸢怔怔地捂嘴。
豫靖侯在看造车,日光下冷脸。
文鸢一早上观察他,反而被他说了:“公主有空,帮我一件事。”
郿弋公主幽禁,正等早饭。
文鸢端来叁菜一汤,还帮她析水果。她絮絮问着你家豫靖侯如何,言语是否提到郿弋之类,看清文鸢后,脸上有狰狞,片刻之间,戾气复现。
“你是亡人?”
“吃早饭了,郿弋姐姐。”
郿弋要抓文鸢。文鸢躲开。
“你敢叫我姐姐,”她切齿,“我明白了,息再篡位,你与他苟且,如今有了地位。”
文鸢说那是五年前的事,况且自己本身就是公主。郿弋不听,凭空求助柳夫人:“母亲,倾旧卢贵族人力,能否帮我杀了他们。”又追问文鸢为何在此,勾引豫靖侯否。
她像婴儿,毫无道理。
文鸢想起过去,起身要走。郿弋大叫。两人都吓一跳。
“你干什么。”
“我收碗。”
郿弋不让收,拿餐具投人,扑在文鸢身上:“我好久没见外面了,我比你更白皙。你知道豫靖侯喜爱白皙!”
“与他无关,郿弋主,”文鸢放下她的手,开始收碗,“你被囚一千八百天,没有新的所爱,这样专情,不如早为亡人,下泉拜见淮海主与西平王,让他们割离骨肉给你。”
郿弋主惨白脸色:“你说什么。”室外聆听的豫靖侯也张口结舌。
下一次大叫,郿弋碎碗,欲切断文鸢的脖子,他进去挡了一下,用流血的手拉着文鸢离开。
两人走得不一致。文鸢很快就喘。豫靖侯转身抱她,架上肩膀。
文鸢推拒,被他捏了下巴,按在一室当中。
“敢以西平王、淮海主为胁,还怕两人之子吗?”
他皱眉笑,文鸢以为他生气,几次躲闪,看他的眼,又惊疑:他没生气,不如说兴奋异常;他的手指尖也烫,从下巴移至脸颊,抚摸她:“你倒是很厉害,我最近才认识你。”
他推她进殿,扯落帷帐,不让她到处挣;一手控着她,一手挽两下衣服,勒住流血处。
陌生的人,文鸢想。
以前他这样乱来,她知道他在做什么,现在却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