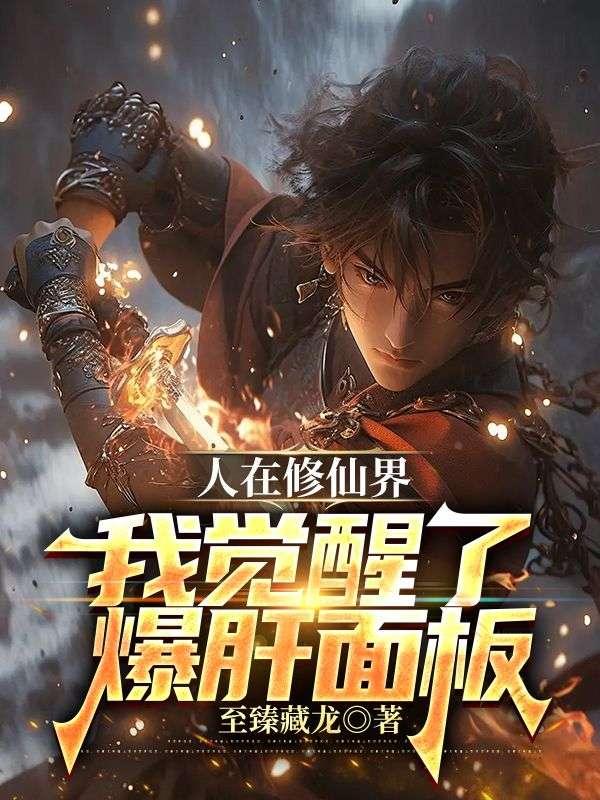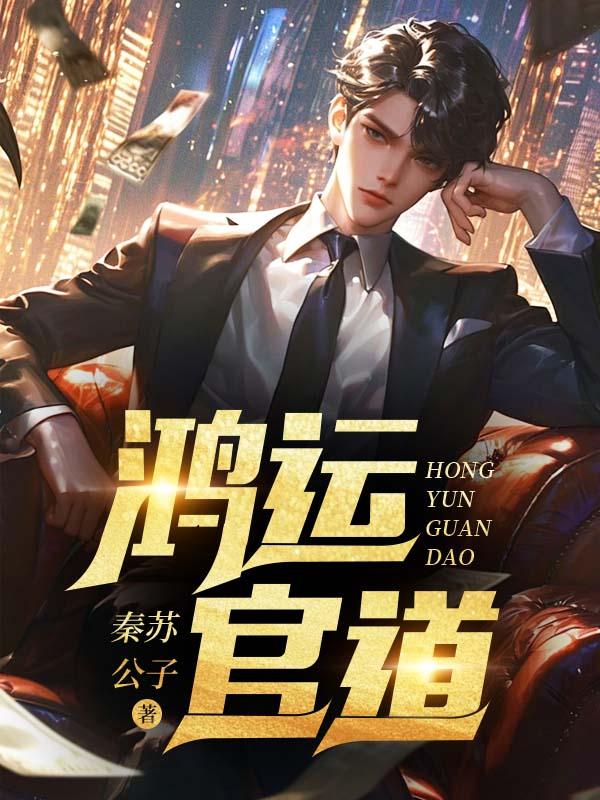落伍文学>双生夫郎互换人生后 > 第205章 哥组京城生活日常2(第2页)
第205章 哥组京城生活日常2(第2页)
当官久了,各有朋友。三五成群的,今天你来,明天我来,又生出许多口角。谢岩口才不错,也没一般文人那么要脸,别人讲话含蓄内敛,主打一个阴阳怪气。他说话就是要戳人肺管子。
都说文无第一,在翰林院比文采,没必要。碰上年长的,谢岩说年龄。碰上同龄的,谢岩说成就。总体来说,三元及第就是他的骄傲。谁能在他这个岁数,拿到他这个成绩,再来跟他讲文星魁斗。
如此这样舌战群儒数月,他在翰林院就没人招惹了。
同届入翰林的榜眼和探花都在苦哈哈挨使唤,被埋在书籍堆里熬日子的时候,谢岩已经实现看书自由。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毕竟他真的没什么差事。领了修书的差事,也是校对较多,不需要他一页页的翻阅。这让他很爽快。
他也会拿问题去请教人。别人计不计较他不知道,反正他不计前嫌,可以当做无事发生,去找人聊学问。
而他师父又说对了,官场就是人精聚集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若非结下死仇,今天见面互喷口水,明天又笑呵呵是亲密无间好同僚了。双方各不计较,还真亲热起来了。
谢岩把翰林院当成大型书院,把他与人相处的经历当做功课,时常给府城写信,说给他师父听。
当然,他是个孝顺的好学生。他到翰林院,最先翻找的是棋谱。考虑到他师父可能看过这些棋谱,所以他也养成了到处找人下棋的好习惯,随缘抓几个,碰见有意思的棋局,就画下来给他师父看。
可能是这个孝顺行为刺痛了崔大哥的心,谢岩听话,返京以后从未主动招惹崔大哥,但崔大哥隔三差五就要来找他一回。
如今过了三年,谢岩也习惯了。
文书间隔着来,他写一写,再看看书,途中起来遛遛弯,再回值房,校对校对书目。午后同样的流程来一遍,一天就过完了。
当官会变得寂寞。这和他后来交友时的感觉一样,再是志趣相投,也不敢轻易说心里话,聊学问的时候,也会再三斟酌用词,怕一不注意,就说了些大不敬的话。
因此,谢岩又常去找崔二哥辩论。整个京城,他最能信得过的人,竟然是这位极为严肃的师兄。
还有一个原因,谢岩并不懂如何当一个合格的严父。他只能去找人模仿。
在他看来,崔二哥就很合适。严肃又正义,看起来有威严,待人却和善。他照着样子来,效果还不错。
这天,熬过上午的差事,他转道出门,去找崔二哥吃中饭——晚上就没空了。
来时不凑巧,崔大哥也在。师兄弟三人聚在一起,小小的谢翰林不怯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
崔大哥让他收拾收拾,可以准备去礼部当差了。
谢岩很感兴趣。他师父给他定好计划了,说他的圣宠来得快,他这几年办了些差事,都不错,都挨夸了,却没有一点升任的消息。
他问:“是图册的原因吗?”
崔大哥摇头,说:“礼部要管科举的事,乡试过后,又要筹办会试、殿试,十月还有万寿节,忙得很,正好缺人手,把你弄进去,你跟着忙一阵,等明年殿试后,有些人就要升迁调走了,你刚好留下顶缺。”
谢岩给他敬茶,“多谢大哥。”
他真是没有上进心,三年才出翰林,混到礼部去当个小官,跟着打杂,还笑呵呵道谢。
崔大哥又拿话揶揄他,“还不是老头子催的,不然我才懒得管你。”
谢岩不懂崔家父子的关系,看崔大哥的性情,便觉得他自小没少挨训斥,现在肯定是对崔伯伯又爱又不好意思言说,只好来挤兑他。
谢岩不与他计较,转而跟崔二哥说:“这个好,不用早起上朝,我能多睡会儿。”
已经习惯夜半三更起床的崔家兄弟:“……”
这小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句中听的话。
他俩也有事找谢岩。
这样清闲的人,不拿来用一用,实在可惜。
他们想让谢岩多带几个学生。带学生,就要带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性子稳当成熟了,懂得一些道理了,知道刻苦了,教起来省事。而这个岁数的学生,由着他们挑,选个聪明机敏的,教着舒心。
启蒙是最难的,性子不定,教又不听,也不懂许多道理,还倔。
他俩还没退下来,忙得很,没空哄小孩,交给谢岩了。
谢岩拿着筷子,再看两位崔哥哥的脸和两鬓发白的头发,心中情绪复杂。
平常喊着大哥二哥,把人喊年轻了。这两个都是跟他父亲一般大的人,如今他有孩子了,两个崔哥哥也当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