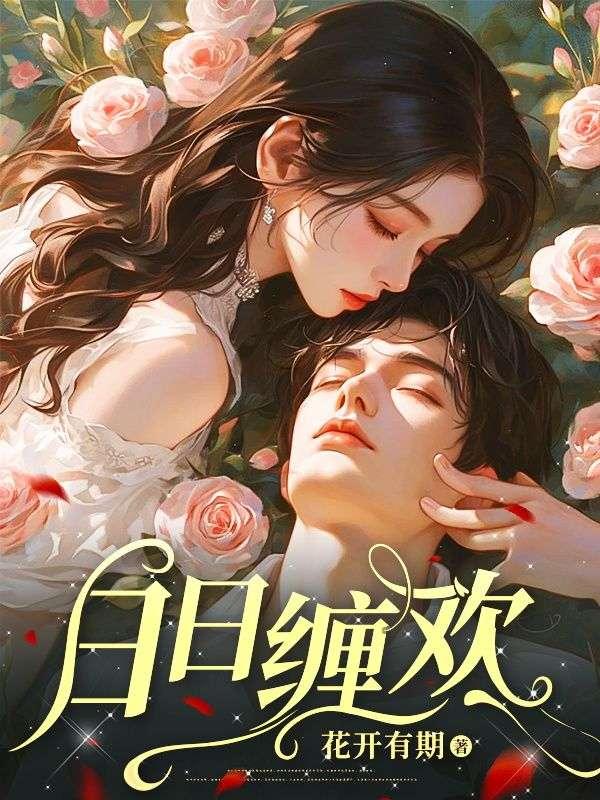落伍文学>谁来言说夜晚 > 第139章 归巢(第2页)
第139章 归巢(第2页)
很难想像这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洸州的迁徙,自古这类逃亡似的人口迁徙总与“水旱蝗汤”相关。金乌名城的居民们收拾好了一家一当,用三轮车、用木板车装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排成一条长龙,携儿带女地往前走。不日金乌名城里的这些违建高楼就得爆破拆除了,尘将归尘,土终归土。
其实他们也闹过,可闹不抵用啊。被双开的市长,被追责的法官,丢了档案的房管部门受了处罚,就连法律上无需为整件事情负责的锦地集团都给予了业主们一部分出于人道主义的补偿金。够意思了。
何况,就连媒体都集体缄默了,包括最爱凑民生热闹的《南城周刊》。最近新闻里都是奥运相关,全省74名奥运健儿即将奔赴北京的消息令所有粤人大感振奋。盛宁其实能够理解,经历了汶川地震这样巨大的伤痛之后,人们是该找个方向重新振奋起来的。
也许这样一场有组织、具规模的迁徙,本就是一次体恤的温驯的抗议。
只是金乌名城的这近万口人还是太少了。
这些业主里经济稍好的还能继续租房住,但盛宁知道,还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人,确实得想法子去桥洞底下占个好位置了。
缓慢移动的人口长龙中,盛宁又看见了哑巴的妻子与儿女。母亲拉着车,哥哥跟着跑。婉君似的小女孩则坐在一颠一颠的板车上抱着父亲的黑白遗像,眼里再没有了那种天真又善良的奇亮。
车轮忽然陷在了一只雨后的泥坑里,盛宁便走上前,帮助女人扶了一把。
“不用了。”女人回过头,冷冷地回他。
告别吱嘎吱嘎的搬家的队伍,盛宁又来到了新密村,也是同样一番荒凉景致。无所事事的农民们围在田边抽烟、打牌,而田里那些插了半蔸的“华早35号”因为无人照料,都死绝了。
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无能为力,伤口更疼了,他只能继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盛检?”突然有个脆亮的声音这么唤他。
一张很青春的、一笑一靥的漂亮脸庞陡然出现在路边。这个女孩有些忐忑地问:“盛检,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儿来了,盛宁想起曾经看过的女孩的档案,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高雪卉,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开学就读高一啦,”女孩眉眼飞扬,特别骄傲地补上一句,“我考上了省重点呢。”
“已经出分了?”盛宁想了一下,中考好像刚刚结束。
“我是提前录取的,数学竞赛拿了奖。”女孩解释说,“那件事情之后,我得把过去浪费的时间都补回来,我学得比谁都认真。”
两人正说着话,一个与女孩年纪相仿的男孩推着自行车出现在了小路尽头,朝女孩所在的方向挥了挥手,笑容十分腼腆。而女孩也看见了男孩,立马两眼发亮,害羞地朝盛宁耸了耸肩膀。
看上去有段青涩的感情即将萌发。盛宁一下由这对可爱的少年人想到了当年未经世事的姐姐和她的初恋沈司鸿。他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去怀念自己的姐姐了。自揭伤疤总不是明智之举。
“盛检,我得走了。”在男孩的呼唤下,高雪卉不得不离开了,但她仍像他们上回在病房里初见时的那样,依依不舍地再次回头,向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检察官郑重致谢,“盛检,谢谢你。”
盛宁点点头,微笑着说,“去吧。”
女孩掉头而去,轻快地小跑几步,然后轻巧一跃,就坐上了男孩那辆自行车的后座。看得出来,她已经完全从小梅楼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她的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本不过一米来宽,但因为铺满阳光,瞧着格外宽敞。
盛宁久久伫立原地,微红着双眼,对女孩远去的背影轻声地道谢。
谢谢。